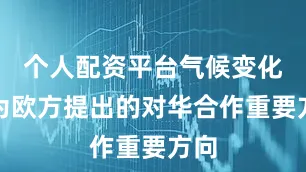2023年3月12日,我与王燕明、张树生一同踏上了回访之路,重返那片曾经插队扎根的第二故乡——刘家坪村。我们怀揣着对青春岁月的回忆,带着对那些曾给予我们无尽恩情乡亲的深切思念,踏进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村庄。
四十多年过去了,昔日的刘家坪大队早已换了模样。曾经狭窄曲折的羊肠小道,如今变成了宽敞平坦的水泥路。过去的土窑洞也被宽敞明亮的新式窑洞取代。四周光秃秃的山峁,如今满是成排的苹果树和枣树,郁郁葱葱,生机盎然。若不是我们当年居住的那几孔窑洞——知青点还被保留下来,我几乎难以相信这里就是当年我们插队生活的地方。
村里的人口十分稀少,半数以上的院落大门紧闭,门上挂着铁锁。我们在村里转了很久,终于与几位坐在村口晒太阳的老人打了招呼,便问起为何这么多房门紧锁。老人们一脸迷茫地告诉我们,年轻人都纷纷进城打工了,许多父母也到城里帮忙照顾孙辈,村里只剩下些老弱病残,整个村的三个村民小组加起来,不足百人。
展开剩余81%起初,老人们没有认出我们,有些人我们也已经记不得了,甚至连名字都模糊了。当我们提及当年北京知青插队的故事时,一位老人凝视我许久,突然喊出了我的名字:“赵和平,你是赵和平!”那声音如同穿越时空的呼唤,让我瞬间认出他正是刘俊德,当年队里的饲养员,如今已八十七岁。我走上前,握住他那双粗糙的手,望着他满头银发和布满沟壑般皱纹的脸庞,心中涌起复杂的情感,泪水不由自主地滑落。
刘俊德大叔也认出了王燕明和张树生,他拉着我们的手,感慨道:“哎呀,转眼你们已经走了四十多年了,我还真认不出来了。来,跟我回家坐坐。”前往他家路上,我们遇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路上打扫卫生,刘俊德大叔喊道:“狗娃,你看看是谁来了?”听到呼唤,那老人回头看了我一眼,随即丢下扫帚,跑到我面前,略显拘谨地擦了擦手说:“和平叔,你们怎么来了?”
若不是刘大叔喊出“狗娃”的名字,我绝对认不出眼前这位老人。他不仅头发花白,背也弯了,口中牙齿寥寥无几。看着他那瘦弱苍老的脸庞,我的心里一阵酸楚。狗娃比我小九岁,三岁时父亲意外去世,是他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拉扯长大。他的真名叫刘明亮,但村里人从不喊他的真名,连比他小的孩子也叫他“狗娃”。
关于狗娃的故事,还得从我们刚来刘家坪大队插队落户说起。1969年1月22日下午,我和另外八名北京知青被分配到刘家坪三队,暂时住进牛棚旁的两孔土窑洞。那时帮我们做饭的是年轻的春梅嫂子——狗娃的母亲。狗娃那年七岁,常跟着母亲到牛棚玩耍。我们都称呼她“春梅嫂子”,她比我们年长十几岁。
狗娃个子憨厚,反应比同龄孩子稍慢,但不笨,会数数能数到五六十。初见他时,我给了几块糖,他见我便会微笑,有时也叫一声“叔”,但很少主动叫。一次我不在窑洞,他偷偷翻了我的提包,被母亲发现后挨了训。他说是想找糖块。初来陕北插队时,姐姐送我一只精致口琴,让我排遣孤独。我虽不懂谱子,也不会吹奏,偶尔随性吹几下,狗娃却很喜欢听,总安静地坐在旁边。
春节过后,气温回升,农活逐渐繁忙。我们学会了自己做饭,春梅嫂子也开始与我们一同劳动,狗娃有时也跟着去山上玩耍。闲暇时,我试图教狗娃识字,可他记性差,学了几天就忘,最后放弃了。三年后的一个秋日午后,社员们在田间休息,我吹起口琴,狗娃忽然抢走了它,胡乱吹奏,引得春梅嫂子生气打了他两巴掌。狗娃没哭,却依旧想要口琴。我将口琴藏进衣袋,装作没看见,他眼巴巴地盯着,好像在无声请求。
刘根旺队长开玩笑说:“狗娃,那山上有个马蜂窝,你要是弄下来,和平叔的口琴就归你了。”狗娃毫不犹豫地奔向那山峁。一个半小时后,他满身是血,双臂划出道道血痕,嘴肿成一条线,眼睛几乎睁不开。看到这情景,春梅嫂子泪流满面,我和刘队长心里都很不是滋味。刘队长更为自己开玩笑惹出大祸感到懊悔。
狗娃站在我身边,盯着口琴衣袋,一言不发。我赶紧将口琴递给他,他没理会春梅嫂子的阻拦,拿着口琴跑开了。看着他,我心疼不已。收工回家的路上,刘队长对我道歉,表示过几天会把口琴要回。我嘴上说不要,心里却有些舍不得。
回到知青点刚做完午饭,春梅嫂子哭着跑来,告诉我们狗娃病了。我们顾不上吃饭,匆忙赶到她家,背起狗娃送往公社卫生院。直到天黑他才醒来,脸和头肿得厉害,手臂也有肿胀。医生说山马蜂毒性极强,他能活下来实属奇迹。十多天后,脸部才恢复正常,胳膊上的伤痕依旧明显。那次医药费由刘队长和我们知青各承担一半。刘队长和春梅嫂子本不同意,但我们认为几块钱的费用不算什么,毕竟春梅嫂子家境清苦。
转眼到了1976年秋天,我幸运地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,赶上了专科大学的末班车,进入天津纺织工学院。离开刘家坪前一天,我将自己的木箱送给了春梅嫂子,洗脸盆、热水瓶等生活用品也一并赠送给乡亲们。离开当天,乡亲们送我到村口,刘队长和狗娃一路护送至公社汽车站。分别时,狗娃拉着我泪流满面,在刘家坪七年多,我极少见他落泪。汽车启动,刘队长和狗娃目送着我离开,目光依依。
此后,我与刘家坪的乡亲们失去了联系。2009年春天,一些当年下乡的同学回访刘家坪,我因身在异地遗憾未能同行。此次重返故乡才知,刘队长早已去世,春梅嫂子也不在了,而可怜的狗娃却一辈子未娶,一人孤独地住在三孔窑洞里。
临别时,我给刘俊德大叔和狗娃各两千元钱,并带去礼物。狗娃坚决不要钱,说责任田已流转,打扫村里卫生一个月有七百五十元收入,生活无忧。见他比我还显老态,我对他说:“你都六十多岁了,以后我不叫你‘狗娃’了,你也别叫我叔,咱俩年龄差不多,你叫我哥吧。”狗娃憨厚地笑着说:“叔,你叫我‘狗娃’就好,村里没人知道我的大名,连娃娃都叫我狗娃。你是我叔,我怎么能叫你哥呢?”他那核桃皮似的脸上难得露出笑容。
那一刻,我心头酸楚无比。多么淳朴善良的狗娃,为何一生孤单?第二故乡的狗娃,成了我难以释怀的牵挂。多年以后,每当忆起他为一只口琴差点被马蜂蛰伤的往事,心头仍旧难安。想到他孤苦伶仃一生,我更觉心疼。愿未来的日子里,狗娃能平安幸福,尽享晚年安宁;也祝愿第二故乡的乡亲们幸福美满,安康常伴。
——作者:草根作家(根据赵和平老师讲述整理)
发布于:天津市国内十大配资平台,配资114查询,配资炒股app最新版本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